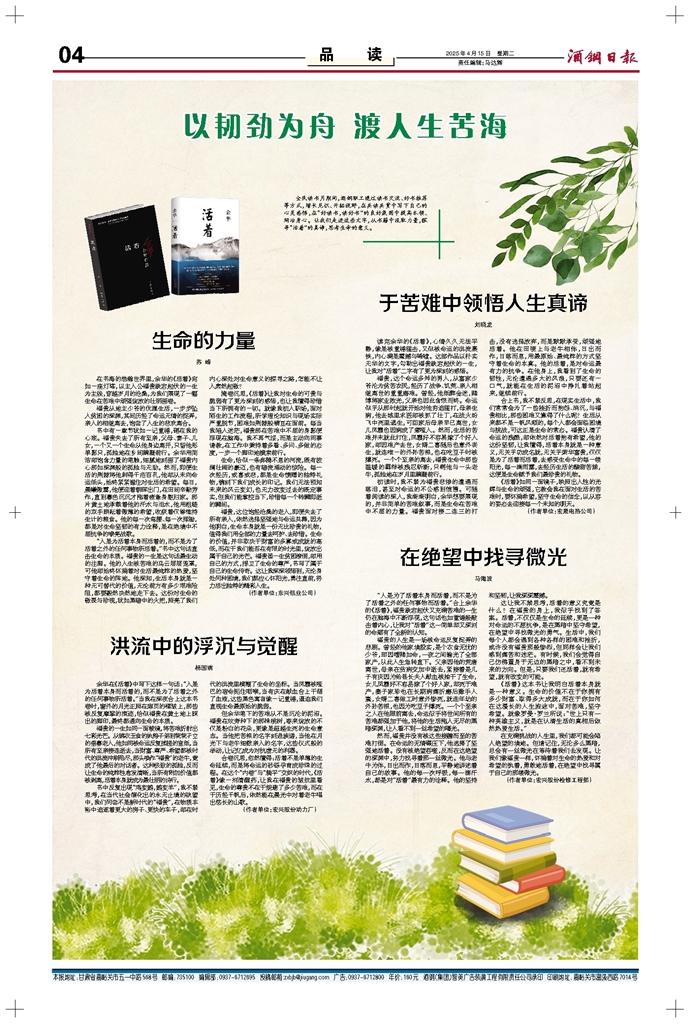余华在《活着》中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,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”当我在深夜合上这本书卷时,窗外的月光正照在扉页的褶皱上,那些被反复摩挲的痕迹,恰似福贵在黄土地上踩出的脚印,最终都通向生命的本质。
福贵的一生如同一面棱镜,将苦难折射出七彩光芒。从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到茕茕孑立的垂暮老人,他如同被命运反复揉搓的宣纸,当所有至亲接连逝去,当财富、尊严、希望都被时代的洪流冲刷殆尽,那头唤作“福贵”的老牛,竟成了他最后的对话者。这种极致的孤独,反而让生命的纯粹性愈发清晰,当所有附加价值都被剥离,活着本身就成为最壮丽的诗行。
书中反复出现“鸡变鹅,鹅变羊”,我不禁思考,在当代社会演化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中,我们何尝不是新时代的“福贵”,在物质丰裕中追逐着更大的房子、更快的车子,却在时代的洪流里模糊了生命的坐标。当凤霞被哑巴的宿命扼住咽喉,当有庆在献血台上干涸了血液,这些黑色寓言像一记重锤,逼迫我们直视生命最原始的脆弱。
但余华笔下的苦难从不是沉沦的泥沼。福贵在坟旁种下的那株桃树,春来绽放的不仅是粉白的花朵,更像是超越生死的生命意志。当他把苦根的名字刻进族谱,当他在月光下与老牛细数亲人的名字,这些仪式般的举动,让记忆成为对抗虚无的利器。
合卷沉思,忽然懂得:活着不是单薄的生命延续,而是将命运的砂砾孕育成珍珠的过程。在这个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交织的时代,《活着》像一剂清醒药,让我在福贵的皱纹里看见,生命的尊贵不在于规避了多少苦难,而在于历经千帆后,依然能在晨光中对着老牛唱出悠长的山歌。
(作者单位:宏兴股份动力厂)